-
 表彰!2024年度中国大学生在线校网通及校园行,这些高校和师生上榜中国大学生在线2024-12-26
表彰!2024年度中国大学生在线校网通及校园行,这些高校和师生上榜中国大学生在线2024-12-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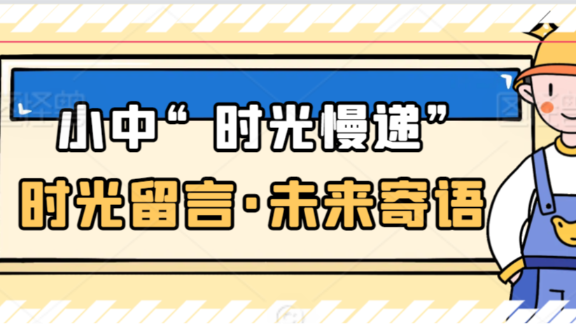 小中“时光慢递”丨时光留言·未来寄语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4-12-05
小中“时光慢递”丨时光留言·未来寄语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4-12-05 -
 青春印记|初入“嘉园”的美好,小中与你一同创造厦门大学嘉庚学院2024-12-12
青春印记|初入“嘉园”的美好,小中与你一同创造厦门大学嘉庚学院2024-12-12 -
 2024校园行 | 河北金融学院原创红色话剧《生死约定》成功首演河北金融学院2024-12-12
2024校园行 | 河北金融学院原创红色话剧《生死约定》成功首演河北金融学院2024-12-12 -
 校园温度记 品渤大温暖渤海大学2024-12-24
校园温度记 品渤大温暖渤海大学2024-12-24 -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同台争辉燃创意 智击键盘竞青春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2025-01-02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同台争辉燃创意 智击键盘竞青春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2025-01-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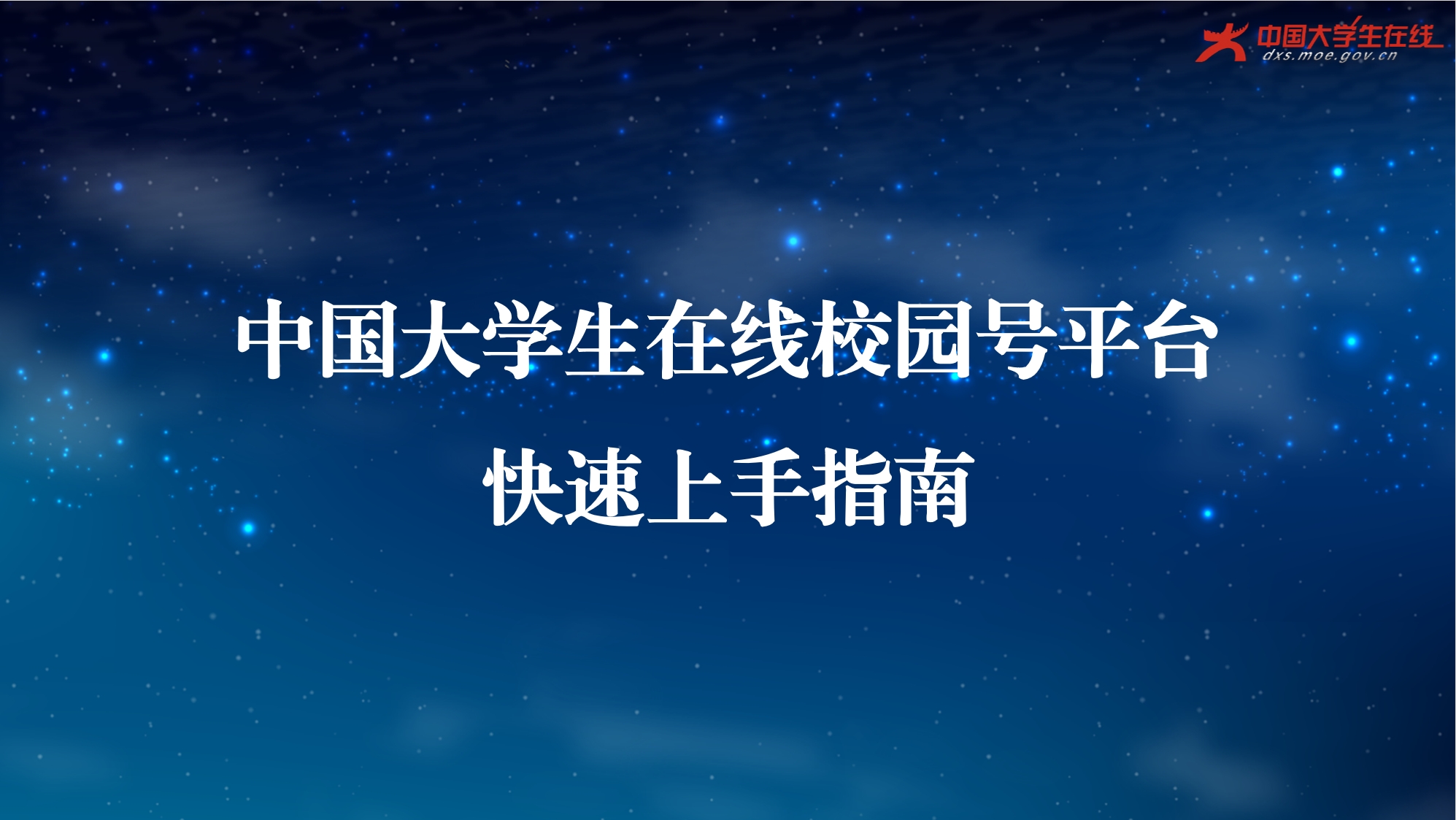 校园号快速上手指南:申请入驻中国大学生在线2025-01-02
校园号快速上手指南:申请入驻中国大学生在线2025-01-02 -
 她说:“教育是热爱和执着,是温柔且有力量......”四川天一学院2024-12-23
她说:“教育是热爱和执着,是温柔且有力量......”四川天一学院2024-12-23 -
 扬思“辩”之雄风,展青年之风采湖南工商大学2024-12-16
扬思“辩”之雄风,展青年之风采湖南工商大学2024-12-16 -
 骄傲!呼伦贝尔学院学子在第11届全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中斩获佳绩呼伦贝尔学院2024-12-19
骄傲!呼伦贝尔学院学子在第11届全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中斩获佳绩呼伦贝尔学院2024-12-19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文化的佳酿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内心的慰籍。它孤独而骄傲,拣尽寒枝不肯栖。文化苦旅是用冷峻的笔调,将厚重的历史推向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与文化再进行一次深邃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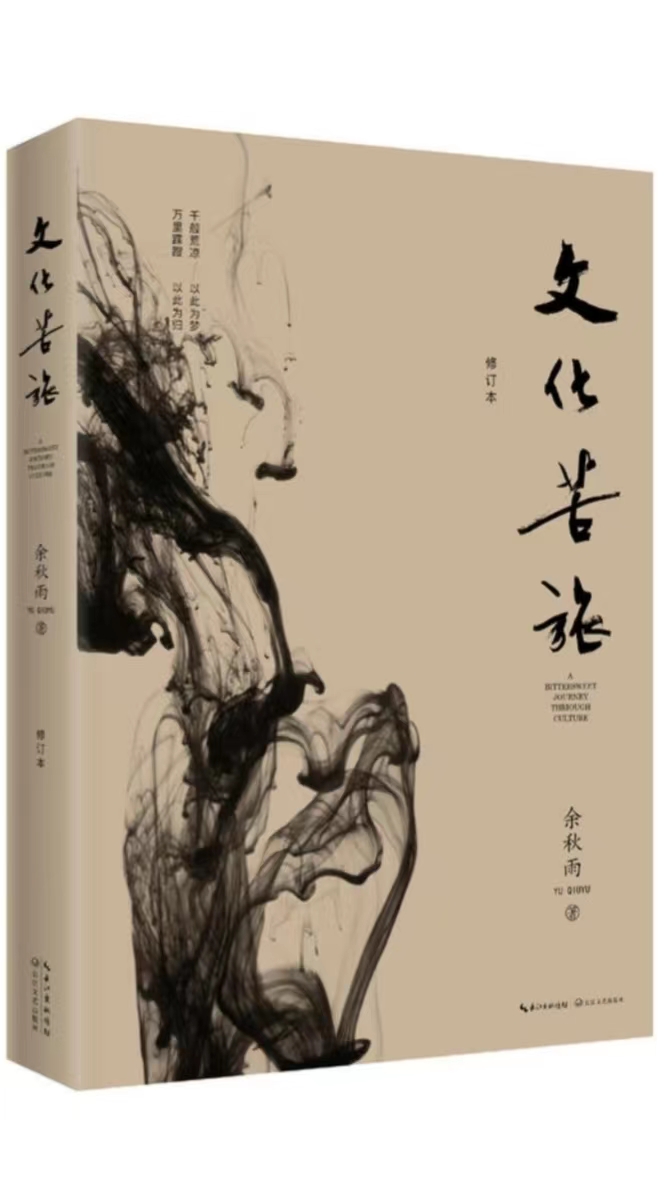
文化从来都是有风骨的,文人亦如此。莫高窟的风沙满天,敦煌的飞天唱着寂寞的歌穿越了千年,一份民族的瑰宝在王道士愚昧的认知里,在无情的白色粉刷中,被运去国外,被毁灭消逝。敦煌学家忍着白眼与嘲笑,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最终让外国无奈地承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他们并没有因为这句话露出任何得意之色,而是站在敦煌前,凝视而沉默。柳宗元贬谪去往柳州,却在自己最后的生命中改变了柳州,使柳州风貌一新,百姓安乐,成为后来贬去柳州文人心里的丰碑,一个荒凉之地成为当地人的世外桃源。

“文章憎命达”似乎是从古到今绕在文人身上的一个魔咒,越是孤独越是绝世。林和靖居于西湖一隅,远离喧嚣与宦海沉浮,梅妻鹤子,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千古绝唱。朱耷冷眼看着山河漂萍,天地寥廓,他笔下孤独的鸟,怪异的鱼翻着令天地为之一寒的白眼,或许无人欣赏无人问津,但是美好不代表幸福,怪异不代表丑恶,遗世独立的精神滋养了后来名传后世的“扬州八怪”,那时官场上汲汲营营身居高位的人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而他们却在青史之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即便潦倒,即便窘迫,文人的心中总会存一抹悲悯。会稽人派出西施迷惑吴王夫差,却在大仇得报后第一件事便是放弃了帮助他们取得胜利又被视为不祥之物的西施。会稽巅上,他们庆祝着胜利。而在苏州,吴王夫差的国度,他们怜惜这位浣纱姑娘,留下了大量纪念的遗迹,于是西施姑娘长久的躲在对方的山巅,存续在口口相传的美好传说里。如今那时的铁马金戈已经消散,但是我们仍会记得西施浣纱池边的风华绝代。

文人是文化最直观最深刻的体现,“清荣峻茂,林寒涧肃”本是写三峡之景,而我却觉得,形容文化最适合不过,百花千色,寒枝落叶,变幻万千。化而为文,署名风貌,邻舟小记,倒也是变幻莫测的文化风韵也。
文化之旅,从来便是厚重苦涩的,是一个民族千百年历练的结晶,是一个民族最独特的记忆,只有特定的人特定的传承才懂。
手抚一盏琴,拨弦而鸣,于洲心桨一叶轻舟;闻远处随风而扬,羌笛声悠悠,泪湿衣衫,仅劝君更尽一杯酒,叹西出阳关无故人。苦旅为何,为此言喻。














